尽管网络游戏(整体画面)是否适合作为“类电作品”(对2020年修改前的《著作权法》以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的简称)或者“视听作品”(2020年修改后的《著作权法》)保护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不少网络游戏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的原告试图以享有著作权的类电影作品或者视听作品为依据来寻求对网络游戏的“整体保护”,而且已经获得了不少法院判决的支持。
但是,如笔者在《呈现于视听作品中的游戏规则依然是思想而并非表达——对若干游戏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判决的评述》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我们可以发现,我国部分法院在涉及游戏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的审理中,把游戏的“具体”玩法规则或情节简单地视同为影视作品中的故事情节,并以该“具体”游戏“玩法规则”具有独创性以及可以被玩家清晰感知或者可以感知特定作品来源为理由,得出其可以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的结论。于是,网络游戏在按“类电作品”进行“整体保护”的名义下,一些法院在判断是否侵权时,虽然根本不进行“动态画面”的比对,却得出了“动态画面”实质相似的结论。因此,其裁判结论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就难免受到影响。
那么,在原告以享有著作权的视听作品为基础来保护其网络游戏的案件中,法院应该如何确定原告所主张的视听作品的独创表达的具体范围,如何识别原告主张著作权的具体内容与其主张的视听作品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何将涉嫌侵权的被告的游戏元素与原告的视听作品进行比对以评判两者是否构成“实质相似”?本文试从视听作品的基本概念特别是视听作品与被制作为视听作品的原作品的关系出发,对此加以阐释,以澄清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一、严格区分视听作品(演绎作品)与被制作为视听作品的原作品
我国《著作权法》有关“视听作品”的称谓经历了三次变化。1990年《著作权法》中称“电影、电视、录像作品(不同于‘录像制品’)”,2001年遵循《伯尔尼公约》的表述改为“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简称‘类电作品’)”,2020年为了消除“摄制电影方法”一词带来的该类作品含义或保护范围上的限制,将这类作品统称为“视听作品”(但其所包含的‘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又有单独的规则)。在谈到“电影作品”与现代种类的“视听作品”的关系的时候,里基森与金斯伯格认为:“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表现的作品”的表述应十分宽泛而足以涵盖“视听作品”,即由“一系列相关画面”构成,借助机器或设备观看的电影或类似作品,如果过去一度曾因“类似方法”要素的限制对需要通过不同固定形式来制作的视听作品能否受到保护提出过质疑的话,鉴于电影摄制中使用的诸多不同介质和方法(如数字电影摄制),电影作品、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表现的作品和一般视听作品之间的区别也就不再具有什么重要意义了。
本文也认为,无论作品类型的名称如何变化,该类作品中可以受著作权保护的“表达”的实质内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都是具有独创性的连续影像画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从美国版权法中移植过来的“视听作品”也未必是个表述该类作品的准确术语,因为“视听作品”的实质是“视”(视觉所感知的影像)而并非“听”——有没有声音,都会不影响视听作品的构成。
尽管不同的国家对这类作品的概念表述也不尽相同,比如德国《著作权法》中的表述和《伯尔尼公约》基本一致;法国为“有声或无声的电影作品及其他由连续画面组成的作品,统称视听作品”;英国为“电影(film)”;美国是“视听作品(Audiovisual works)”,包括“电影(motion pictures)”,但是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法律定义中无一不强调这是由“连续画面(moving image)”或“系列画面(a series of related images)”构成的作品。德国学者认为“电影作品的表达手段是活动的图片(一连串在时间上先后互相衔接的图片),而不像语言作品那样以文字,也不像美术作品那样以线条与构图为表达手段。他们通过前后衔接表达了某个单独的图片所不能表达的内容。正是由于这种特有的表达手段使得电影成为了一种特殊的作品类型”,“电影作品的产生并不是在剧本完成之后对图片衔接的虚构,而是在拍摄工作开始之后才产生。创作性劳动投入体现在把摄制电影所需要的各个作品融入到一个整体之中以及把这个整体转化为图像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德国法保护电影作品著作权,核心也同样是保护导演、摄影师、剪辑师等所创作的连续衔接的“图像”。
虽然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也明确电影作品和类电作品是“一系列有伴音或无伴音的画面组成”的作品,也就是说,视听作品的独创性表达就是体现在有声音或者无声音的连续影像画面上,但是,一些法院在审理具体的侵犯视听作品著作权的案件中,却未必能牢牢把握住这个基本概念,比如,有时候会把剧本、音乐等作品也当作是“视听作品的一部分”来保护了,这就偏离了视听作品的内涵和本质,把视听作品本身和那些为了制作视听作品而使用的各种作品混为一谈了。本文认为,只有从原作品与改编演绎作品的关系的角度去理解“为了制作视听作品而使用的各种作品”与“视听作品”的关系,并将其贯彻到网络游戏保护的司法实践中去,才能走出这个误区。
首先,摄制权属于演绎权的范畴。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摄制权,即以摄制视听作品的方法将作品固定在载体上的权利。这里“将作品固定在载体上”中的“作品”就是“为了制作视听作品而使用的各种作品”,而“以摄制视听作品的方法”进行“固定”的行为,虽然不排斥是以复制或者录制的方式,但因为这种“固定”的结果其实是产生了一个新的“视听作品”,所以“摄制视听作品”的“固定”本质上就是在原有作品基础上演绎或创作产生一个新的作品。
其次,从《伯尔尼公约》文本的历史发展来看,即便最初电影被看作是已有作品(特别是戏剧作品)的复制品,但是1908年的柏林会议已经将这种电影复制品“作为一种类似于翻译而值得保护的转换形式对待”,电影成为一个独立的享有著作权保护的对象(而不仅仅是特殊形式的戏剧作品)的主要理由也是“摄制电影的复制方法不仅仅是简单的复制;制作电影需要对已有作品的摄制方式作出完整的一系列判断,将它固定在胶片上仍然会使它成为完全不同的结果,在这一方面,‘改编’一词可能更适宜用来描述摄制方法和作为摄制结果的电影片”,1928年的罗马文本第14条第(3)款与柏林文本相比进一步明确“电影作品(的保护)不得损害被复制或改编的作品的作者的权利”,这里的“改编”一词 “强调了一个基本事实:在对已有作品的大多数电影加工中,要求作出更适合于称为改编而不是复制的重要变动和修改,因此,无论是复制还是改编均足以使产生的电影构成原创作品”。可见,正是因为摄制电影不是一个简单的机械抄袭或复制,而是创作出了新的作品,因此,摄制行为其实就是改编或演绎行为,摄制形成的视听作品就是一个不同于原作品的新作品。
再者,上述分析也可以从德国学者对电影作品的阐释中得到印证。比如,雷炳德认为:“那些为了制作电影所使用的作品应当与电影作品作出区分。这里涉及电影作品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各种作品,比如小说、戏剧、歌剧或者那些为了拍摄电影而制作的电影剧本或者专门为电影而制作的音乐作品等。为了制作电影作品而对这些作品的使用行为在法律上统称为电影摄制——不管是否对那些作品作出了更改或者进行过演绎处理和改编”,“电影摄制是对被使用作品的一种复制,同时也是对这些作品的一种演绎。即使是对所使用的的作品未加任何改动或者仅仅作了些不重要改动的情形下,也属于一种演绎,因为通过电影摄制行为就把所使用的作品从原来的作品类型转化为另外一种作品类型,这种转化过程必须要由某种创造性劳动来完成”。
可见,视听作品本身属于改编作品的性质,因此《著作权法》中有关改编作品的规则也应该同时适用于视听作品,特别是涉及视听作品与制作视听作品中所使用的其他作品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比如,我国《著作权法》第13条规定:改编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从这个规定中可以看出,在一个改编作品中其实存在着“双重”的著作权,一个是原作品的著作权,一个是改编作品的著作权,其权利分别属于原作品的作者和改编作品的作者(改编者),我们不应该把原作品的独创性表达和改编作品的独创性表达混为一谈,既不能以改编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来替代原作品的著作权保护,也不应该把原作品的作者视同为改编作品的作者。比如,德国《著作权法》明确区分电影作品的作者(包括导演、电影摄影师、剪辑师、音响师等)与电影作品中原作品的作者(Stoffwerkautoren),因此,剧本、音乐的作品的作者并非电影作品的作者。
但是,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七条却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都笼统地视为一个“整体”的视听作品的作者,于是,视听作品的著作权保护似乎就可以涵盖剧本、音乐等作品的著作权保护了。在这样的规则“指引”下,我国法院在视听作品保护的司法实践中就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将视听作品与用于制作视听作品的其他作品混同起来的思维,将视听作品的保护延伸到“其他作品”的保护上去了,由此很可能导致一些判决说理的混乱和裁判结论的错误。在以视听作品保护网络游戏设计(特别是游戏的规则和玩法)的案件中,有的判决以保护“视听作品”的名义直接去保护那些“视听作品(网络游戏)”中所内涵的角色形象、音乐声响、场景地图等设计元素,甚至去保护那些很可能属于思想范畴的游戏规则、玩法、数值等,其实就已经陷入了上述误区。
二、对演绎作品(视听作品)的保护必须要排除原作品的干扰
如前所述,虽然在一个改编作品中确实同时并存着原作品的著作权和改编作品的著作权,但是,这两个权利并不是交叉的,而是各自独立的,绝不意味着原作品作者可以对“改编作品本身”享有著作权,当然也不意味着改编作品作者可以对原作品享有著作权。原作品的作者只能就改编作品中所内涵的原作品享有著作权,改编作品作者则只能就改编作品中那部分“新”的独创性演绎享有著作权。我们虽然无法从物理上将改编作品与改编作品中内涵的原作品进行简单的切割,但是,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改编作品的独创性表达与原作品的独创性表达必须从理念上加以区分。在一个涉及侵犯改编或演绎作品著作权的纠纷案件中,我们应该以这样的区分来分析被告涉嫌侵权的作品是否利用了原告(演绎作品著作权人)作品中的独创性表达,如果不进行这样的区分,就很可能会陷入裁判的误区。
在最高人民法院再审的涉及被异议图形商标“ASOO”是否侵犯米高梅电影片头“雄狮标识”图案的在先著作权的案件中,无论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高行(知)终字第2738号行政判决,还是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一中知行初字第4464号行政判决以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评字(2014)第07041号《关于第7241616号“ASOO及图”商标异议复审裁定书》都认为被异议商标与米高梅公司享有著作权的“雄狮标识”作品在设计手法和整体视觉上几乎无差异,构成实质性近似,被异议商标侵害了米高梅公司的在先著作权。
虽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注意到米高梅公司主张在先著作权的创作完成及发表时间为1987年的“雄狮标识”其实是该公司在距今五十年之前就使用的“雄狮图形”基础上演绎而来,但由于新标识与原来的“雄狮图形”之间能够体现不同作品的独创性,所以依然作为一个“新”的演绎作品予以保护。但是,问题在于:当原告以这样一个新的演绎作品来主张著作权的时候,该演绎作品中所内涵的原作品的独创性表达事实上已经因为超过著作权保护期而进入公有领域,而二审判决在进行侵权比对的时候,依然是以“整体”视觉上“不存在明显差异”为由而认定“构成实质性近似”,却没有将那些已经进入公有领域的原作品的独创性表达剔除出去,说白了,这样的侵权比对方法其实是以“整体”的演绎作品的名义保护了本来不应该受到保护的“内涵”的原作品。
正因为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案的再审判决中指出二审法院的“事实认定显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这个案件的曲折过程充分说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改编作品或者演绎作品仅仅是在改编或者演绎上体现的独创性表达,而不能把原作品的独创性表达也当作演绎作品来保护——哪怕原作品依然在著作权保护期限内,否则就会不恰当地扩大演绎作品的保护范围,从而导致不合理的裁判结论。
视听作品作为一个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保护,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在判断被告的行为是否侵犯视听作品著作权(实质性相似的判定)的时候,应该要排除被告的单幅画面、情节故事、音乐等“非连续画面”与原告存在实质相似因素的干扰,在判决中不能以单幅画面、情节故事、音乐的实质相似来分析评判连续画面的实质相似,甚至直接据此得出侵犯电影作品著作权的结论。假设B制片人根据A创作的电影剧本拍摄了一部电影(经过A授权),C制片人擅自根据A创作的同一电影剧本拍摄了一部电影(未经过A授权)。因为两部电影的情节故事是一样的,所以连续画面的呈现过程以及演员的表演过程看起来也是差不多的,但C确实是自己雇佣了导演、摄影师、演员等而重新摄制新的连续画面,C制作的连续画面侵犯B制作的连续画面的著作权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C侵犯了A(电影剧本)的著作权,但不太可能侵犯B(原电影作品)的著作权。 总之,对电影作品的保护,是保护其在连续画面形成中的独创性表达,因此,在侵权判定中法官所要关注的只是被告是否利用或复制了原告的连续画面的独创性表达,而并不是比对画面背后的故事情节是否一致——这是电影剧本保护的问题了。
然而,在网络游戏按视听作品进行“整体保护”的名义下,一些法院在判断是否侵权的时候,虽然根本不进行“动态画面”的比对,却得出了“动态画面”实质相似的结论。在“《我的世界》诉《奶块》”游戏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原告主张“《我的世界》游戏整体画面是具有独创性的连续动态画面” ,并认为被告的“《奶块》游戏呈现的整体画面高度近似”,但是,其所谓“游戏整体画面”的高度近似却是从“游戏机制、方块设计、元素设计、交互设计(外观、功能、组合规则等)等高度相似”中得出的结论,这种权利主张显然也是在保护“游戏整体画面”的名义下悄悄地转移了其所要保护的核心内容——连“游戏机制”“功能”“组合规则”这种显然难以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内容也纳入了其主张的权利范围里面去了。而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在分析被告的《奶块》游戏与原告游戏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的时候,虽然把“权利作品”确定为是“整体动态运行的游戏画面”,但是,在侵权比对的时候,却并非是对两个游戏的“整体动态画面”进行对比,而仅仅是将原告“列举的112个游戏元素与《奶块》游戏中对应的游戏元素”进行对比,并基于“名称、来源、功能、合成规则都存在高度近似,甚至完全相同”,就得出了被告游戏“在运行中所展现的动态游戏画面与权利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的结论。然而,“名称、来源、功能、合成规则”的相同就意味着“动态画面”的相同或实质相似么?更何况,“名称、来源、功能、合成规则”是可以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吗,还是其实是属于无法获得著作权保护的 “思想”?这样的问题,一审判决都没有进行分析,一审判决甚至没有对被告提出的两个游戏的“整体画面、颜色搭配、规则设定、UI界面风格均不相似”抗辩意见进行过任何评判,就得出了“动态游戏画面构成实质性相似”的结论,因此,其裁判结论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就难免受到影响。
三、结论:以视听作品保护网络游戏规则必须比对连续画面
网络游戏作品虽然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视听作品,但是网络游戏作为视听作品保护并不存在实质性的法律障碍。如果原告向法院请求依据视听作品来保护其网络游戏,就应该遵循《著作权法》保护视听作品的基本规范,而不能以网络游戏的“特殊性”而改变《著作权法》所规定的视听作品的内涵——连续影像画面。
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电影作品的制作者确实可以统一行使电影作品以及被用以摄制成电影的其他的作品的著作权,因此,网络游戏权利人也确实可以按制作者的身份对网络游戏中内涵的不同作品统一地行使著作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网络游戏中的任何一个设计元素都可以不加区分地按视听作品进行保护,网络游戏中的单一设计元素最多不过是用于制作视听作品的其他作品,而是否构成其他作品依然需要按照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构成要件进行逐一评判。
视听作品既是一个合作作品,也是一个演绎作品,如果原告坚持以视听作品来保护所谓的游戏玩法或规则,那么,在侵权比对的时候,法院就必须排除不属于视听作品独创性表达的其他作品或设计元素的干扰,而应该责令原告举出连续影像画面构成实质相似的证据来证明被告对其游戏玩法或规则的抄袭。如果原告只是以文字表述或者单幅图像作为证据来进行比对,就已经偏离对视听作品保护基本规则了,法院不应该支持这样的证据,而应该驳回其诉讼请求。
总之,以视听作品保护游戏玩法规则,原告不能只举证文字或单幅图像,法院也不能只比对文字或单幅图像,而必须比对连续影像画面,否则,就不是对视听作品的保护,而是对文字作品或美术作品的保护了。比如,在琼瑶诉于正的《宫锁连城》电视剧作品侵犯其文字作品著作权的案件中,原告琼瑶主张的是文字作品《梅花烙》的著作权保护,因此在判定侵权的时候,就不是比对电视剧的连续影像画面,而是比对剧本中的故事情节或桥段这样的文字表达了。
注释:
1.有观点认为,网络游戏与传统电影无论是在表现效果还是在创作过程上都高度相似,可以将其纳入电影作品的类别进行保护,玩家的交互性操作并不会影响网络游戏整体画面的定性。参见王迁、袁锋:《论网络游戏整体画面的作品定性》,载于《中国版权》杂志2016年第4期;有的观点则认为, 游戏画面的可能性不能穷尽,网络游戏不符合类电作品的本质,相比于单机游戏,网络游戏难以被划分为类电作品中去。参见:孙磊:《网络游戏画面构成类电作品吗?——与王迁、袁锋老师商榷》,载于“知产力”2016年10月13日。
2.张伟君:《呈现于视听作品中的游戏规则依然是思想而并非表达——对若干游戏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判决的评述》,载于《电子知识产权》2021年第5期。
3.里基森、金斯伯格:《国际版权与邻接权——伯尔尼公约及公约以外的新发展》,郭寿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76页。
4.范长军(译):《德国著作权法》,第2条,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5.黄晖、朱志刚(译):《法国知识产权法典》,L.112.2条,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页。
6.5B Films (1) In this Part "film" means a recording on any medium from which a moving image may by any means be produced.
7.“Audiovisual works” are works that consist of a series of related images which are intrinsically intended to be shown by the use of machines or devices such as projectors, viewers, or electronic equipment, together with accompanying sounds, if any, regardless of the nature of the material objects, such as films or tapes, in which the works are embodied.
8.“Motion pictures” are audiovisual works consisting of a series of related images which, when shown in succession, impart an impression of motion, together with accompanying sounds, if any.
9.雷炳德:《著作权法》,张恩民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4页。
10.里基森、金斯伯格:《国际版权与邻接权——伯尔尼公约及公约以外的新发展》,郭寿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9页。
11.里基森、金斯伯格:《国际版权与邻接权——伯尔尼公约及公约以外的新发展》,郭寿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71页。
12.雷炳德:《著作权法》,张恩民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155页。
13.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2017)最高法行再11号。
14.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0106民初13437号。
15.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高民(知)终字第1039号。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知产财经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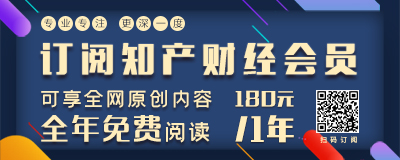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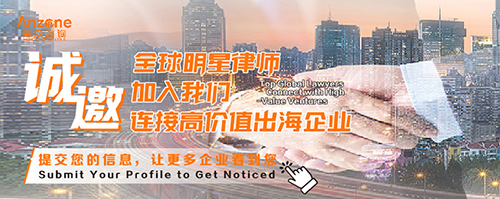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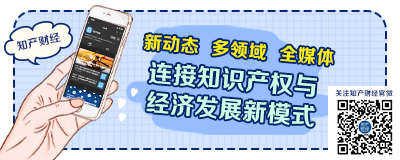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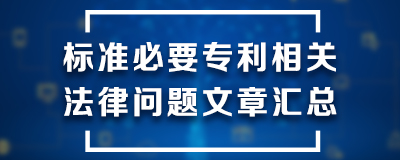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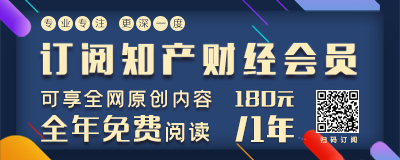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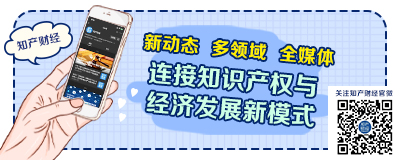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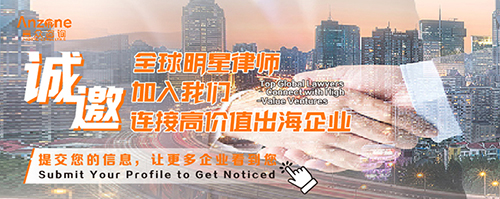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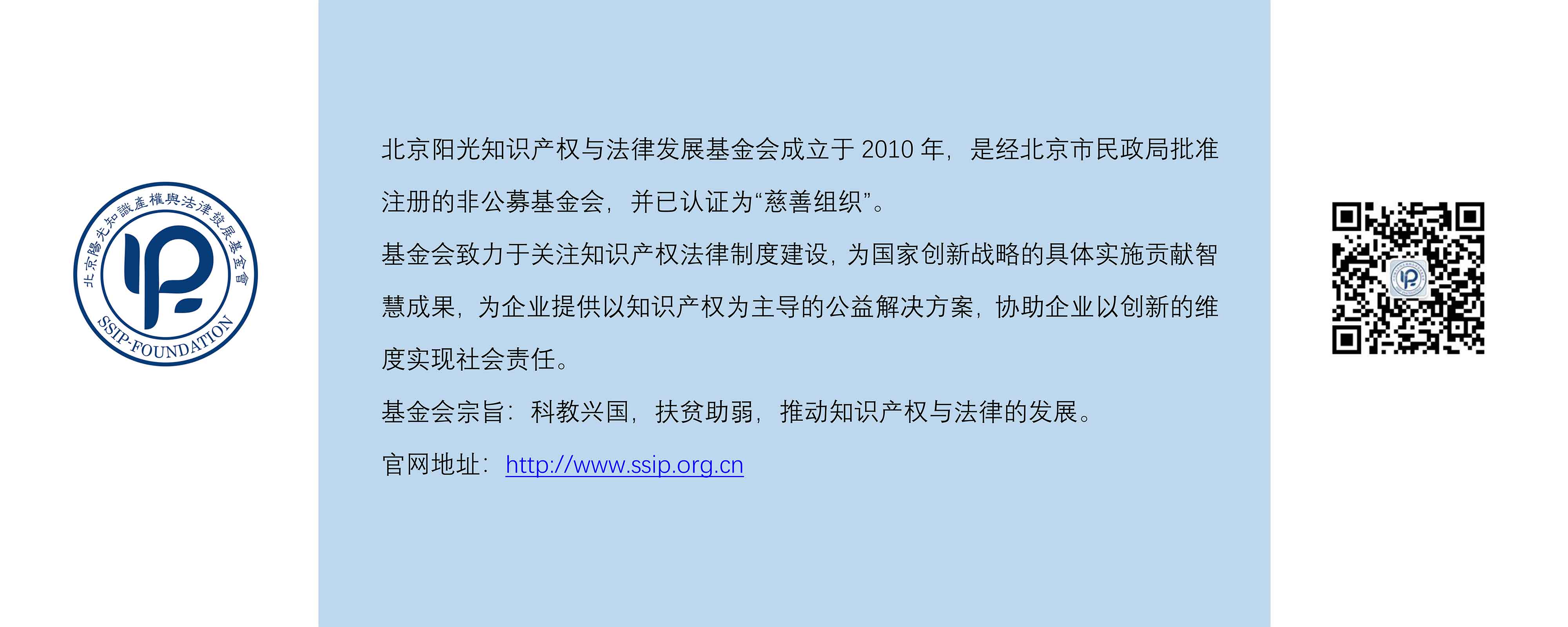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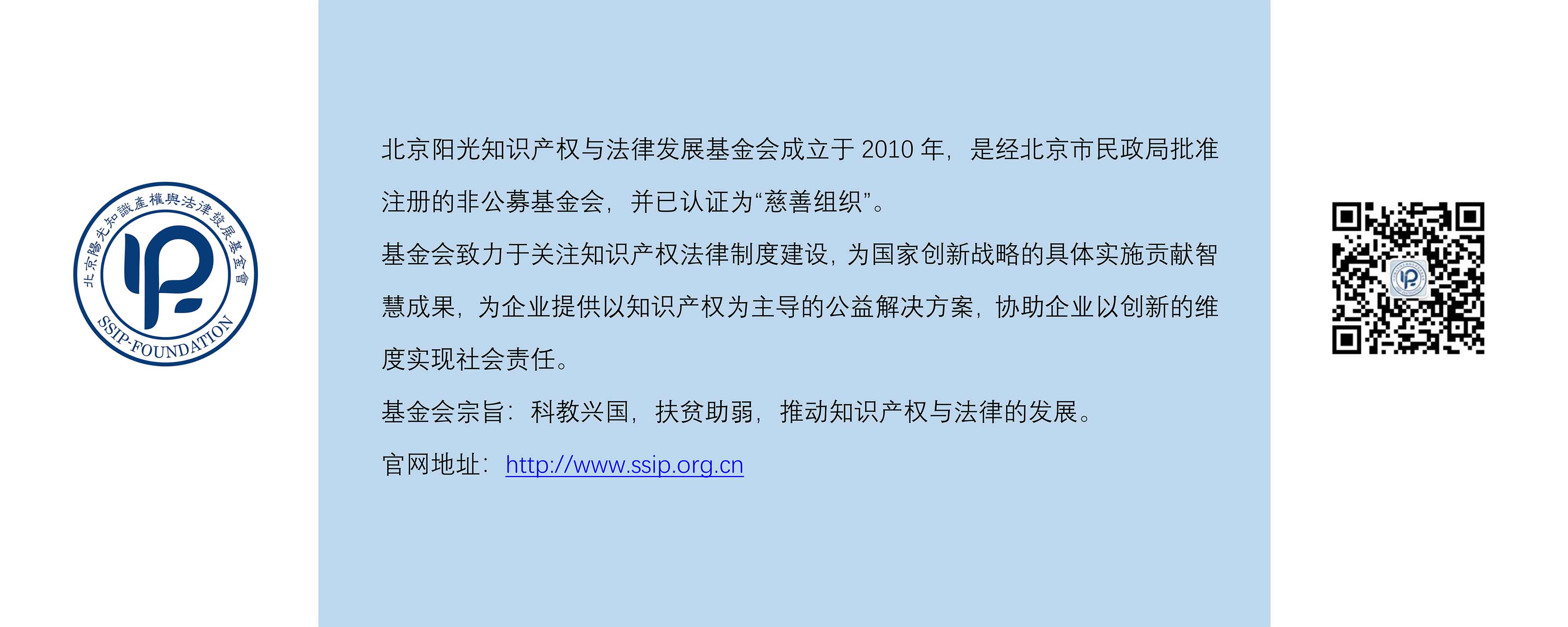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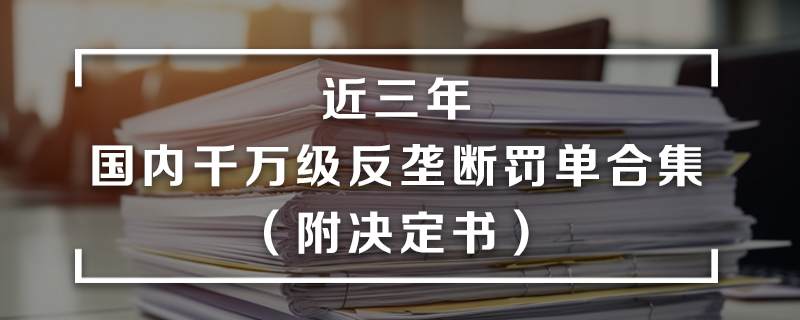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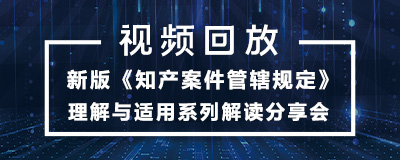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