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艳芳(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
摘要:混淆行为居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之首,2017年和202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均将其作为重点条款,不断明确其法律定位和完善内容。经历次法律修订,混淆行为条款经历了由混杂到单一、由仿冒标识行为到市场混淆行为以及由封闭性规范到开放性规范的立法转变,形成了以所有混淆行为为调整对象、以足以产生市场混淆为根本要件并兼有开放性和排他性的制度架构和法律定位。混淆行为条款并不限于商业标识的混淆,还应包括其他任何混淆行为以形成一种领域性法律调整的闭环,并应当排除依照一般条款认定同类行为,因而呈现出“自身违法”、领域性与排他性的法律特性。在竞争自由与竞争公平不同模式之下,《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的适用应当坚持市场混淆的强约束,选择竞争自由的政策目标和价值取向,防止泛泛地依据“搭便车”“不劳而获”之类的公平竞争观念,不适当地扩展商业标识或者相关商业成果的保护范围。
关键词:不正当竞争行为;混淆行为;商业标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反不正当竞争法
来源:《法学家》2025年第5期“主题研讨二:《反不正当竞争法》前沿问题探讨”栏目。
因篇幅较长,已略去原文注释。
目录
引 言
一、我国混淆行为的法律架构及其当前适用中的突出问题
二、《巴黎公约》规定与混淆行为的法律定位
三、立法政策选择与混淆行为的法律定位
四、行为类型化的法律功能与混淆行为的定位
结 语
引言
混淆行为是最为古老、最先类型化、最被普遍承认和最为重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大陆法国家反不正当竞争法自始承认混淆行为自不待言,即便迄今仍不承认存在一般性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英国等普通法国家,也存在涵义相当甚至范围更为广泛的“passing off”(仿冒行为)。古老的混淆行为不断地应时而变和历久弥新,至今仍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行为类型,仍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居于重要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将混淆行为置于第二章列举规定的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之首,并在2017年和2025年法律修订中作为重点修订条款,其重要性不言而喻。2025年6月27日表决通过的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混淆行为”有较大幅度的修订,除增加部分具体商业标识类型外,尤其是增加了混淆行为的类型,并明确了商业标识权利冲突和搜索关键词混淆行为的法律构成。我国混淆行为规范在与时俱进地发挥重要功能的同时,也不断地面临新挑战,为应对其在适用中不断产生的新争议,最为重要的仍是准确厘定其法律定位。鉴此,本文拟结合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混淆行为条款的变化,对混淆行为的制度框架和法律定位加以探讨。
一、我国混淆行为的法律架构及其当前适用中的突出问题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自制定以来历经多次修订,其混淆行为条款通过2017年和2025年两次重要修订,经历了由混杂到单一、由仿冒标识到市场混淆以及由封闭到开放的立法转变,至今已日臻完善,形成了以商业标识及其他混淆行为为调整对象、以足以产生市场混淆为法律底线并兼有开放性和排他性的制度架构和法律定位。
首先,由规范对象的混杂不一到单一性混淆行为的法条内容转变。2017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删除了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规定的注册商标一项,将误导性宣传归入相应的法条之中,因而成为纯粹的混淆行为条款。法律条款的独立和纯粹,使其调整对象的领域更为明确和突出,更易于识别其适用边界和法律定位。2025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使混淆行为条款的内容得到进一步完善。
其次,由仿冒商业标识到混淆行为的法律定位转变。2017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在序文中明确定性为“混淆行为”,且规定了“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后果要件。在第6条中,除第1—3项对未注册商标、市场主体标识和互联网标识分别作出规定外,第4项的兜底性规定还可以涵盖商业标识混淆之外的情形,旨在规范所有符合第6条属性的行为。修订后第6条与《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以下简称《巴黎公约》)的混淆行为定位更加一致。下文将要讨论,这种定位转变不仅是调整范围和适用对象在量上的变化,更是在立法政策上的“质变”。2025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则进一步强化了混淆行为的定位。
再次,由穷尽列举的封闭性规定到概括兜底的开放性规定。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列举的商业标识的具体类型,且没有“等”“其他”之类的概括性表述,所适用的商业标识范围有限。2017年修订后的第6条改为“等”字概括规定加兜底条款,不仅可以涵盖除注册商标以外所有商业标识,还可以容纳商业标识以外的其他混淆行为,因而能够支撑下文讨论的商业标识等混淆行为调整的领域性和排他性。
综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混淆行为条款历经多次修订,不断地被赋予新内涵和增强涵盖力,持续适应新情况和应对新问题,至今仍保持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但是,混淆行为条款当前在法律适用中仍存在一系列难题和争议,比较突出者如下:(1)混淆行为条款是否意味着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将足以产生市场混淆作为认定一类商业标识或者商业成果的模仿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底线,除此之外的模仿行为均纳入自由竞争的范围。特别是,对他人商业标识的“搭便车”式利用(如关键词搜索隐性使用),或者对他人商业成果的逼真模仿(或者称为盲从模仿),是否当然构成不正当竞争,是否需要达到足以混淆的程度。例如,“歌莉娅服装款式案”二审判决根据是否具有识别商品来源意义,对服装款式加以区分:能够识别商品来源的服装款式纳入2017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的保护范围;不能识别商品来源的服装款式,因其属于经创作设计形成的一种商业成果,可以纳入第2条一般条款予以保护。问题在于,不属于专门权利又不具有商业标识意义的服装款式,以构成商业成果进行一般性保护,在法理和立法政策上是否具有正当性。(2)混淆行为是否限于或者专指商业标识混淆,以及是否均以商业标识具有“一定影响”为要件。例如,有一定独特风格的时装款式刚上市即被模仿,虽不满足“一定影响”要件,但又感到不公平需要加以保护,能否以2025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第1款的兜底条款加以保护,或者转向适用第2条一般条款,还是属于公有领域而不予保护?下文讨论的关键词搜索广告隐性使用他人商业标识的定性争论亦涉及此类问题。(3)商品化权益等商业成果能否纳入混淆行为的保护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涉及准确厘定混淆行为的法律定位及其背后的竞争法理念。
二、《巴黎公约》规定与混淆行为的法律定位
《巴黎公约》对混淆行为采取穷尽式的开放性定位,即对商业标识持开放性态度,并穷尽所有市场混淆行为的可能。我国是《巴黎公约》成员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混淆行为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巴黎公约》,但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混淆条款规定并不到位,2017年、2025年修订的混淆条款已回归到《巴黎公约》的定位。
(一)《巴黎公约》的混淆行为规定
混淆行为是《巴黎公约》最先明确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反不正当竞争条款之所以纳入《巴黎公约》,是因为早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涉及制止不诚实的竞争者实施滥用商业标识等不公平经营行为,大多数行为与工业产权法所禁止的行为相当,因而被认为属于工业产权保护的组成部分。
1900年修订《巴黎公约》时引入了反不正当竞争条款,但没有就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明确列举。在1925年海牙修订会议之前,受到重点关注的是制止欺诈性商业竞争行为,此次修订后,《巴黎公约》形成了一般条款与列举性条款并行的架构,然而不正当竞争的内容仍局限于针对商品的市场混淆和商业诋毁行为。例如,第10条第1项、第2项分别为“以任何方式造成与竞争者的商品(goods)混淆的所有行为”“在商业中诋毁竞争者商品的虚假表示”。尽管1934年伦敦修订会议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没有就修订内容达成普遍一致,最终仅将行为的适用对象从“商品”扩展为“企业、商品或者工商业活动”。其中,此类混淆可由使用相同或者近似商标或者商号造成,且通常由这方面的特别立法所禁止。使用包装、宣传语、企业的地址和其他特性等造成的混淆,也是如此。诚如世贸组织专家组在“澳大利亚—平装案”裁决中所言,《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3)列举的三类不正当竞争行为是作为最低限度的例子提供的,采用任何手段对竞争者的营业场所、商品或工商业活动造成混淆的一切行为均应予以禁止。
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反不正当竞争示范规定》(以下简称《示范规定》)结合各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情况,对《巴黎公约》不正当竞争条款进行的诠释和细化。《示范规定》第2条规定了“与他人企业或者活动造成混淆”(causing confusing with respect to another's enterprises or its activities),包括第1项的“一般原则”和第(2)项的“混淆举例”。《示范规定》的释义指出,第2条是基于《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3)1进行的规定,混淆可以由“任何手段”造成,第2项只是列举了常见的混淆手段,并非穷尽式列举。
以上表明,《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将混淆行为定位于与他人商品、企业(包括法人和自然人)或其活动“造成混淆”,旨在涵盖任何市场混淆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商业标识的混淆。《示范规定》列举的混淆情形主要是商业标识的混淆,但并不以此为限。因此,混淆行为不限于仿冒商业标识的行为,还包括其他任何市场混淆行为。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混淆行为条款与《巴黎公约》规定的对比
我国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商业标识条款有落实《巴黎公约》混淆行为条款之意,同时也是针对我国的保护需求所作的规定。如起草说明所说,“草案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也同国际惯例基本一致”。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的序文为“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参与立法者在解读时,将该条规定的行为称为“市场交易中的欺骗行为”。但是,欺骗行为显然是一个上位概念,除此之外还涉及误导性宣传、欺骗性有奖销售等行为。《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3)列举的三类行为分别为混淆行为、欺骗行为和诋毁行为,混淆行为包括冒用商业标识等行为,而欺骗行为则是误导性行为,两者均可称为虚假表示(misrepresentation)。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只是对商业标识的混淆行为作出列举性规定,还不能覆盖所有的商业标识及此外的其他混淆行为,因而,其范围小于《巴黎公约》规定的混淆行为。2017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明确将禁止的行为称为混淆行为,且在商业标识的范围和混淆行为的类型上进行了扩展。这种混淆行为的界定已与《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3)的分类和界定相一致。
2017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序文采用的“混淆行为”表述,显然是从结果角度进行的行为界定,从行为特征与结果相结合的角度表现这种行为,就是仿冒混淆行为。“仿冒”是擅自使用相同或者近似的商业标识;“混淆”是“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两者结合起来称为“仿冒混淆行为”,该称谓对该类行为特征的表述更为周全。当然,混淆行为并不限于商业标识的混淆。
2017年《反不正当竞争法》实现由商业标识仿冒行为到混淆行为的转变,本质上重塑了混淆行为的制度架构与法律定位,特别体现为穷尽了任何市场混淆行为。但是,司法实践中对其适用范围有认识上的分歧。一些裁判延续旧有的商业标识仿冒行为惯性,仍将2017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定位于商业标识的保护。如“江南布衣案”二审判决认为,2017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是关于商业混淆行为的规定,被混淆对象应当是有一定影响的标识。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9号,以下简称《若干问题解释》)第13条对2017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第(4)项兜底条款进行了解释并明确列举了两种情形,此两种情形仍然属于商业标识混淆的范畴,且有“一定影响”等要求。但该司法解释并未明确是否属于对兜底条款的穷尽性解释,至少从文义上看易使人误认为兜底条款仍只适用于商业标识的混淆。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混淆行为的规定具有落实《巴黎公约》规定的意蕴,并根据遏制国内市场中混淆行为的需要作出了符合国情的规定。为此,202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应当作与《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3)1一致的法律定位和条文解释。
首先,第7条穷尽了混淆行为的所有情形。2017年修订至今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混淆行为条款虽然未像《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3)1那样采取“以任何方式造成与竞争者的企业、商品或者工商业活动混淆的所有行为”的高度概括性规定,也未完全采取《示范规定》第2条概括加列举的规定,而是采取列举加兜底的方式,即第1—3项是对三类商业标识的列举性规定,并另设第4项兜底规定,既涵盖了各类商业标识,又有兜底条款,其立法模式相当于《示范规定》第2条第2项。202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应当作与《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3)1相一致的解释,即将其定位于混淆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商业标识的仿冒混淆行为,此外还包括其他造成与市场主体及其活动产生混淆的行为。而且,对于第7条的解释可以参考借鉴《示范规定》第2条的规定。鉴此,《若干问题解释》第13条对于2017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第4项兜底条款的解释,应当理解为仍属针对典型情况的举例性规定,并未穷尽兜底条款规定的适用情形,仍可能在此之外存在其他未列举的混淆行为。
其次,第7条划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商业标识以及制止其他混淆行为的法律边界。基于自由竞争派生的自由模仿原则,不属于知识产权范围的商业标识或者商业成果,原则上允许他人利用和模仿。利用和模仿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应当以混淆为底线性要件,并需到达市场混淆的程度;不构成混淆的情形则属于自由竞争的范围,应当排除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范围。例如,“费列罗巧克力案”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一方面明确基于市场经营与自由竞争,经营者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借鉴并进行创新,以形成有明显区别的各自商品的包装、装潢,另一方面也强调不能对商品特有包装、装潢进行全面模仿,如导致市场混淆、误认则会构成不正当竞争。
再次,在造成混淆的适用对象上,第7条序文中的“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应当作相当于《巴黎公约》规定的“企业、商品或者工商业活动”的解读,包括市场主体、商品或者工商业活动的混淆。
三、立法政策选择与混淆行为的法律定位
202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是否穷尽并排斥第2条一般条款对于商业标识的保护,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和做法,根本上涉及立法者选择的立法政策问题。
(一)司法实践中的分歧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是否穷尽并排斥第2条对于商业标识的保护,当前的分歧主要体现为关键词搜索隐性使用他人商业标识的法律定性,以及时装新款式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等领域。
“海亮案”再审判决关于关键词隐性使用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认定,推翻了此前多数判决趋于共识的观点,导致司法裁判的转向并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和比较热烈的讨论。问题的关键是,使用他人商业标识不构成2017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规定的市场混淆,可否以“搭便车”等为由再按照第2条予以认定。“海亮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为,未经许可擅自将竞争对手的商业标识设置为关键词进行使用的行为,即便是不产生市场混淆的隐性使用,也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所规制的不正当竞争,即不仅损害了竞争对手的商业利益,亦扰乱了正常的互联网竞争秩序,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准则。
近年来,涉及服装款式抄袭的不正当竞争案通常涉及刚刚上市尚不具有“一定影响”的服装款式,在确有保护必要时,是依据当时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还是第6条加以保护,法院存在不同的裁判态度。这既涉及商业标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否一概纳入第6条调整,又涉及不具有“一定影响”的标识能否纳入第6条兜底条款之中。例如,“江南布衣案”一二审判决均以商业标识仅应依据第6条保护为前提。再审判决认为,服装的款式和款号不属于受知识产权专门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保护的客体,但如果仿制行为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的适用条件,则可适用一般条款予以规制。“秘思任类服装店案”二审判决认为,被告直接搬用原告的模特展示商品图片、还使用“xx原版”表明款式来自涉案品牌的行为系不劳而获攫取原告劳动成果,依据第2条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爱帛公司案”一审判决认为,被诉批量仿冒同款服装样式行为属于第6条第(4)项足以产生市场混淆的行为。
以上案例所涉司法裁判的观点分歧,涉及商业标识保护是否仅由混淆行为条款进行穷尽性保护,202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是否仅限于“一定影响”标识的保护,以及所涉商业标识因不能认定“有一定影响”而不能纳入第7条之时,可否依据第2条进行保护。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涉及第7条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定位以及深层次的立法政策选择问题。
(二)混淆行为立法政策的国际观察
综观国外反不正当竞争立法和实践,在立法政策和价值取向上大体有两大流派,即普通法国家偏向于维护竞争自由和注重消费者选择,通过混淆的刚性要件限制不正当竞争的范围;大陆法国家偏向于保护竞争者和维护一般意义上的公平,对于市场竞争相对地干预较多。当然,两者是相对而言,也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划分,各国情况差别较大,且两者有相互接近的倾向。
法国等大陆法国家常常将公平目标置于竞争目标之上,甚至被批评为反竞争;英美等普通法国家更为推崇竞争和竞争自由,将竞争作为首要目标,只有在竞争者的行为达到极端时才被认为构成不公平。竞争者的行为可能误导或者使消费者混淆所提供的商品的来源或者性质,才可以归入极端行为。两种方法均同时考虑消费者和竞争者的利益,但普通法国家一般将消费者利益置于首要的位置。相比之下,大陆法国家在讨论不正当竞争时通常更少关注消费者,更多关注一般性的竞争者的“公平和诚实”行为,强调公平的竞争观。正是由于对反不正当竞争法宽泛的解释,使得在有些情况下将商标置于极为尊崇的地位,使其成为一种近乎道德权利的东西。
两种基本取向的差异,体现了普通法国家的“passing off”(仿冒行为)与大陆法国家不正当竞争之间的文化冲突。基于上述两种立法政策和价值目标,就商业标识(注册商标和未注册商标)保护而言,不同的国家存在法律制度背后的文化差异。有些国家突出重视防止欺骗消费者的狭窄政策目标,而有些国家将消费者保护目标置于更大的管制竞争目标之下。普通法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由狭窄的消费者保护目标所主导,而大陆法国家坚持更为广泛的不正当竞争观念。
1.普通法国家
在Hodgkinson & Corby Ltd. v. Wards Mobility Services Ltd.案中,英国的雅各布(Jacob)法官承认普通法仿冒侵权行为(tort of passing off)与更为广泛的(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原则之间的重要差别,即“此种侵权行为从未显示出丝毫游离于欺骗情形以外的趋向。若真超出这一范畴,就会进入诚实竞争(honest competition)的领域,并以欺骗以外的原因被认定为非法。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因,我无法想象。这只能扼杀竞争。”“不存在复制的侵权行为。不存在夺走某人的市场或者客户的侵权行为。市场和客户都不是原告自己的。不存在以此种方式利用他人声誉的侵权行为。不存在竞争侵权行为(no tort of competition)”。在此,清晰表达了将不构成混淆的商业标识使用行为认定为非法,只能扼杀竞争的观点。
当然,普通法对不正当竞争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假冒行为(passing off)是构成普通法中不正当竞争的核心,其当今的救济范围较之几十年前已大大拓宽,方式是逐渐扩展其下列三个主要构成要素的能力:声誉、混淆以及损害或者损害的可能性。声誉不再严格限定于单一的业务或者企业。经营者需要证明其受保护的辖区内具有声誉的要求,相较于在其他国家有极高的声誉,在许多普通法国家已经有所放松。混淆也成为一个可塑的变量。甚至在100年前,对于混淆的界定已超出商品来源的混淆,将销售真品但并非对其商品来源而对于商品质量(如二手货)的误导行为,纳入假冒行为的范围。近年来,法院甚至还引入了“售后混淆”“初始关注”混淆。除将利润损失作为损害外,普通法法院引入了交易机会的损害,适用于非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行为,如商标法中引入的淡化行为。接受“反向混淆”的概念,作为假冒行为的一个变体,表明普通法法院是如何扩张法律的范围,而将实际上并不混淆和不可诉的侵占行为,变成可诉的行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Dastar v. Twentieth century Fox案中甚至认为,此种情形更像是侵占行为(misappropriation)而不是混淆,即未经许可取走了别人创造的东西。
在决定是否救济虚假表示行为时,普通法国家的法院强调公共利益,即确保“不正当”竞争不能损害经营者之间残酷的合法竞争自由。Harman法官对此进行了描述:“一个经营者对另一个经营者的损害是竞争后果的本质所在。一个质优老鼠夹的制造商让人踏破门槛去购买,此举必然损害在先质次制造商的业务。除非这些制造商能够支撑,否则将被悲惨地逐出市场;但这是市场竞争的应有之义,也是资本主义世界能够成功的推动力。这是一个绝对的根本假定……这种被诉的侵权实际上一直在竞争,只是加了句古老的童谣哭声‘这不公平’。对此,我会回应一句我保姆的绝佳建议:‘这世界是个非常不公平的地方,不久你就会了解得更多’……在我看来,不正当竞争不是对一种已有不法行为的表述。造成某种损失的竞争也不公平,因其破坏了现有的法律权利。但是,有效的竞争并不因此而不公平。”
普通法国家对于不正当竞争持限缩态度的主要原因是追求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以及界定其与知识产权的关系。首先,担心宽泛的不正当竞争可能损害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如英国Deane法官在Moorgate案中指出:“无论是法律原则还是社会效用均不要求或者值得消除……法律或者衡平的限制和保护与自由的竞争之间的边界,即负责任的国会……通过在易于夸大的概括性之下引入确定其允许范围的诉因,决定在竞争诉求与政策之间的适当平衡,使法官形成何为市场公平的独特观念。”普通法国家要求法院在反不正当竞争上的谦抑,是为了不让法官在更为敏感的政策问题上干预太宽,以便将其留给国会决断。其次,更为实质性的理由涉及知识产权与自由竞争的关系。所有的独占或者准独占权利都被视为憎恶垄断而偏好自由竞争的一般原则的例外。专利、版权、商标和外观设计有确定的边界和专门立法。如英国法官Dixon在Victoria Park Racing Co. v. Taylor案中所说:“英国司法区域内的衡平法院并不对具有交换价值的所有无体价值物均给予禁令救济的保护。这些无体价值物可以是个人运用其智力、知识、技术和劳动之类的能力、资源和经营活动的产物。版权法的历史以及发明专有权、商标、外观设计、商号和声誉均足以表明,这些特殊的利益均纳入专门的名目之下进行保护,而不是通过宽泛的概括规定。”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International News v. Associated Press案(以下简称INS案)多数意见判决试图将不正当竞争救济扩展到侵占行为。撰写判决稿的Pitney大法官采用了貌似具有吸引力的“不播种而收获”的观点。但是,该案判决后来基本上未被尊重。美国的不正当竞争法主要涉及假冒行为和相关的经济侵权行为。除了少数例外,美国法院忌讳形成任何强有力的不正当竞争侵占理论。如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v. Sports Team Anylysis and Tracking Sys. Inc.案巡回法院判决指出,INS案判决限于其特殊的事实,在原告的“热点新闻”被侵占时才能够给予保护,并阐述了“热点新闻”原则的具体限定适用条件。
2.大陆法国家
大陆法国家总体上持宽泛的不正当竞争观念,特别是在侵占行为和寄生模仿行为的规制上持宽松态度。例如,法国在不正当竞争行为中纳入“经济寄生主义”(economic parasitism),在现代社会中提供适当的救济。许多国家倾向于在被告不必要地“盲目抄袭”(slavishly copies)以攫取原告产品利益时进行干预。但是,在大多数国家普遍奉行的原则是,仅仅是复制并不构成不正当竞争。对于并无虚假表示的侵占行为,通常不能构成不正当竞争。构成不正当竞争还需要更多的额外因素,问题在于如何确定这些额外因素。
3.文化和法律观念影响关键词搜索行为的法律定性
关键词搜索行为的定性是典型的文化和法律观念差异的体现。例如,法国是最为遵从公平优于竞争观念的国家,法国法院(如斯特拉斯堡法院)很早就有判决认定,关键词广告隐性使用他人注册商标不构成商标侵权,但依照《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构成不正当竞争。德国法院则认为,使用竞争对手的公司名称作为关键词,不构成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有些案件提交欧盟法院裁决,但只涉及商标侵权问题,不涉及不正当竞争。2010年欧盟法院发表过三个意见,认为广告主使用关键词属于商标使用,如果可能导致混淆,就有侵权的可能性,但涉案谷歌关键词并不产生混淆。将该问题提交欧盟法院的法国、奥地利和德国均未提及不正当竞争问题。在荷兰法院提交裁判的第四个案件中,对于成员国法院能否依据“不正当竞争利用或者损害商标的显著性或者声誉”禁止关键词广告,欧盟法院认为不必涉及这些问题。在2009年英国法院提请欧盟法院裁决的Interflora案中,提出了在关键词广告中未经许可使用他人商标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的问题。该案涉及谷歌基于普通法和大陆法国家对于商标保护的差异,其中,在英国和爱尔兰采取了比较激进的关键词广告政策。2011年欧盟法院首次裁决认为,不仅要考虑由关键词广告引发的商标请求,还要考虑不正当竞争请求。就商标请求而言,使用 Interflora商标系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的“双相同”,此时商标受到“绝对保护”。如果使用Interflora商标可能“对商标的功能产生不利影响,不管是识别来源的基本功能还是其他功能,如保障商品或者服务质量的功能,以及交流、投资或者广告功能”,就可能要承担责任。如果不属于相同商品或者服务,是否承担责任取决于使用Interflora商标是否容易产生商品来源的混淆。在该案中,欧盟法院认为关键词广告并不损害商标的广告功能,并让英国法院自行决定被告的行为是否损害商标的投资功能,即是否损害该商标能够吸引消费者并维持其忠诚的声誉的能力。欧盟法院还让英国法院决定Marks & Spencer对于Interflora 商标的使用是否损害该商标的显著性,但损害要达到消费者可能将该商标视为送花服务的通用名称的程度。与以前的裁判不同,该案中欧盟法院还考虑了未经许可使用Interflora商标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特别是此种使用是否构成“没有正当理由……不公平利用商标声誉的显著性”,而构成非法的“搭便车”。法院可以轻而易举地认定,关键词广告旨在通过商标的显著性和声誉谋利,广告主从其未经许可使用他人商标以吸引消费者注意,而消费者随后可能从广告主的商品或者服务之中受益。剩下的问题就是这种获益是否不公平。在此,欧盟法院直接援引L'Oreal案中的分析,认为在关键词广告中使用他人商标可能缺乏“正当理由”。尽管欧盟法院留给英国法院决定如何基于案件事实适用该标准,但欧盟法院认为,如果广告主提供的商品系模仿商标所有人的商品或者服务,就“特别可能构成”不公平。相比之下,如果广告主只是对于商标所有人的视频或者服务提供一种替代性选择,那么关键词广告应当被认定为具有公平性。因为,为消费者提供一种替代选择构成援引竞争对手商标的正当理由。可见,就不正当竞争而言,Interflora案表明,确定广告主的商品或者服务是“模仿”还是“替代性选择”至关重要。至于两者的区别何在,欧盟法院未进一步阐述。
前些年美国法院对于关键词广告使用他人商标是否构成“商标使用”,存在争议。答案可能取决于他人商标仅仅作为触发广告之用(隐性使用),还是在广告结果上使用(显性使用)。即使构成显性使用,还要依据多种因素对于是否构成混淆加以分析。可以确定地说,美国法院在决定广告词使用是否侵权时,并不考虑当事人之间的商品或者服务是模仿还是替代性选择问题。近年来,美国法院的判决以是否构成混淆为标准,认定关键词广告使用他人商标是否构成商标侵权。如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新近判决的Lerner & Rowe PC vs. Brown Engstrand & Shely LLC案继续遵循该院2011年Network Automation,Inc.vs. Advanced Sys. Concepts,Inc.案判决确立的法律框架,对于商标侵权问题进行评估,并将争议聚焦于“混淆可能性”,最终认定ALG使用“Lerner & Rowe”商标不会造成消费者混淆。显然,美国法院是在商标侵权框架内解决将商标用于关键词广告问题,若行为不构成商标侵权,则不再另行审查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也即商标法已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穷尽式调整。
综上,尽管各国个案裁判的司法态度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在以消费者为取向的国家,倾向于更多地维护竞争自由,对于将他人商业标识用作关键词广告的行为,通常以市场混淆作为根本的衡量标准,隐性使用通常不构成市场混淆,因而不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特别是不构成商标侵权之时,不再进一步考量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倾向于将公平置于自由之上的国家(以法国为代表),除考量市场混淆标准之外,还将“搭便车”作为不正当竞争的构成要素,隐性使用关键词即便不构成商标侵权,也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欧盟法院虽然采取宽泛的商标使用概念(损害他人商标功能即为商标使用),也允许在不构成混淆性商标侵权之时继续进行不正当竞争的评价,但这种不正当竞争条款本来规定于欧盟商标法之中,对于构成不正当竞争的条件有较为严格的限制(如对于淡化商标显著性的损害程度有较高要求),总体上呈现出一定的折中性倾向。当然,国外的情况可以供我国比较参考,但选择哪种态度,最终取决于我国的立法政策和价值取向。
4.我国的立法政策和价值取向
关键词搜索所使用的商业标识包括注册商标和此外的企业名称等商业标识,因商业标识的不同而涉及两类法律问题。第一,使用注册商标首先由商标法调整,然后再涉及不正当竞争问题,这就涉及商标法能否穷尽对注册商标的保护以及商标法与注册商标的关系。认定因不构成市场混淆而不构成商标侵权的判决,有些不再进一步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衡量,而是依《商标法》穷尽对注册商标的保护;有些则在认定不构成商标侵权之后,继续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衡量,并依据“搭便车”等市场混淆以外的理由,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如“海亮案”再审判决)。而且,后一种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调整的判决,显然首先涉及《商标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然后又涉及在当时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之外依据第2条在不构成市场混淆的情况下延伸保护注册商标。第二,隐性使用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有些判决依照当时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以是否混淆为判断标准,不构成市场混淆的情况下认定不构成不正当竞争;有些判决在不构成市场混淆的情况下依照第2条认定不正当竞争。这些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立法政策和价值取向的不同理解。否定观点是基于竞争高于公平的竞争观,而肯定观点则是基于公平高于竞争的竞争观。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的定位
202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定位于市场混淆行为,坚持市场混淆标准。为更好地维护竞争自由,可以将第7条的立法政策解读为穷尽了包括商业标识之内的所有市场混淆行为,不构成市场混淆的商业标识使用或者其他模仿行为,不再依据第2条认定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这种解释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更多走向维护竞争自由和追求市场效率的国际趋势,也符合当前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实际。例如,根据《若干问题解释》第1条的规定,对于属于第7条调整范围而不符合其适用条件的,不应当再纳入第2条的认定范围。司法实践中以保护商业成果、制止不劳而获等理由,在不符合第7条适用条件时再依照第2条保护,实质上是抛弃了市场混淆的底线,转向了宽泛地承认商业成果侵占行为、逼真模仿之类的宽保护。
如果将第7条定位于采取混淆的底线标准和追求竞争自由的政策目标,那么在搜索关键词隐性使用他人商业标识时,即使行为人有客观上的“搭便车”和占便宜的情形,也属于自由竞争的容忍范围,不构成不正当竞争。对于不具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纳入第7条第1款第4项兜底条款之内。例如上述时装款式款号等模仿行为,通常是原告持续推出的系列服务款式,整体上已累积了显著的商业声誉,即便其刚刚推出的时装款式也会很快被市场认可,加之考虑到时装的流行性和快消费性特点,在不能认定“有一定影响”时根据第7条第1款第4项加以保护,既能够符合兜底条款的“足以引人误认为”的保护条件,又能够妥善处理第7条和第2条的法律调整关系。据了解,当前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在不具有“一定影响”时不敢适用第7条第1款第(4)项,主要是囿于第7条仅保护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识的认识,但在特殊情况下仍有保护的必要,才绕开第7条而选择适用第2条,这实质上导致了第2条和第7条适用关系的紊乱。在澄清第7条并不以保护一定影响的商业标识为限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四)《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第1款第(4)项的界定
《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3)1并未将混淆行为仅限于商业标识混淆,而是定位于任何混淆行为。为此,《示范规定》第2条对于混淆行为作出广泛的解释。许多国家亦是如此定位混淆行为。如日本和韩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均广泛界定混淆行为,认为其“产品或者服务标识混淆”的规定与《巴黎公约》的混淆行为一致。如在一个模仿歌手外貌的案件中,2009年1月韩国最高法院曾经裁定自然人名字可以作为商业标识而受到保护,但歌手的外貌不能视为有资格获得保护以防止模仿的标识。但是,根据后来的《防止不正当竞争和商业秘密保护法》第2.1.k条规定,可以将其纳入保护范围。2017年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增加了第6条第4项,作为规制混淆行为的兜底条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第6条规定的讨论中,有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实践中还存在其他形式的混淆行为,建议增加兜底条款,以防止挂一漏万”,建议增加一项兜底条款作为第4项。这一兜底条款的独特价值,就是直接将商业标识的仿冒混淆条款转变为更为广泛的市场混淆行为。
实践中,确实还有一些不能为202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第1款第1—3项所规制的仿冒混淆行为,规定兜底条款可以实现禁止仿冒混淆行为的全覆盖。可以纳入兜底条款的行为大体上有如下四种情形:(1)仿冒前三项商业标识以外的其他商业标识的行为,即前三项还不能涵盖所有的商业标识。例如前述尚无一定影响的服装款式款号,在特定条件下又可以认定为属于“足以引人误认为”的情形,可以将其纳入兜底条款保护。在“乐町牌女装案”中人民法院认为,服装款式款号不是法定权利和权益,单个款式款号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必须属于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识,本案属于服装款式系列的整体性模仿,应对被告销售相同款式的服装以及使用相同服装款号的行为进行整体评价。案涉服装款式款号并非一个或几个商品,案涉淘宝网店销售的相关服装款式,与原告乐町品牌女装款式在宏观与微观上高度一致,系不低于164款服装的款式款号的全店抄袭与全面模仿。被诉行为容易引起一般公众误认为这些服装款式均来源于原告乐町品牌,或者认为案涉店铺与原告存在服装设计、贴牌代工、许可使用、广告代言等特定联系,构成当时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第4项的行为。(2)商业标识权利冲突造成的市场混淆行为,即不能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第1款第2、3项的商业标识权利冲突行为。这些混淆行为均自成一体和独具一格,不能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前3项所包括。(3)商业标识仿冒混淆以外的商业特征混淆,即主要不是仿冒单项标识,而是通过行为特征的模仿造成市场混淆。有些混淆行为不是擅自使用被仿冒对象的特定标识,而是通过使用多个相关性识别元素构成一种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混淆。此类行为虽然不构成对于特定商业标识的仿冒,但其一系列行为特性达到了仿冒混淆的效果。如“湖南王跃文诉河北王跃文案”,被诉不正当竞争行为本质上属于仿冒混淆行为,但并非冒用特别的商业标识,如商品标识和自然人姓名,而是通过使用河北王跃文真名、编造虚假和误导性宣传资料等综合性方式,达到混淆两个王跃文及其作品、攀附湖南王跃文及其作品声誉的目的。(4)与其他经营者的市场活动产生混淆的其他情形。如对于他人经营方式、促销活动等经营活动进行模仿,足以达到混淆程度的情形。总之,第7条第1款第4项的兜底性规定,使其涵盖了第7条第1款第1—3项未能包括的商业标识,尤其是商业活动标识。这也使该条规定涵盖了除注册商标以外的所有商业标识,实现了商业标识保护的全覆盖。
四、行为类型化的法律功能与混淆行为的定位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行为列举性规定旨在将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化并确定具体的法律边界,实现法律确定性的各种独特功能,并据此界定了包括混淆行为在内的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定位。
(一)类型化行为的“自身违法”、领域性与排他性
总体上说,特定竞争行为的正当性判断取决于复杂的具体情况,要求审查判断既有的或者流行的标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化是增强竞争行为正当性判断确定性的重要方式。为此目的,《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3)1列举了四类需要在国内法特别禁止的具体行为。各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都有其共通的和独特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在法律功能上,这种类型化规定主要有法律定性上的“自身违法”性、调整对象和范围的领域限定性以及与其他法条之间的排斥性(以下概称为“三性”)。
首先,类型化行为的“自身违法”性。这些行为又被解读为“假定的‘不正当’”,相当于自身违法行为,即符合其行为特征就当然违法。类型化行为的目的是穷尽并固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素,实现行为判断上的确定性。
其次,类型化规范的领域性。类型化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看起来有些凌乱,相互之间缺乏先后相继和融贯合一的严密逻辑性,甚至给人“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印象。除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市场竞争属性,或者可以把各类行为统一于“竞争”“竞争行为”的概念之上,其内在的逻辑统一性较弱。在一定意义上,类型化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一个“杂烩”。但是,这些松散的类型化行为恰恰成全了各类行为的独立领域性。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均调整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领域,设定这一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具体界限。2025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就是为商业标识仿冒等市场混淆行为立规,实际上确定了注册商标以外的商业标识仿冒及其他市场混淆的法律边界。
再次,类型化规范的排他性。类型化行为的构成要件本质上是划定不正当竞争与自由竞争的界限,以遏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路径实现更大的竞争自由。类型化行为的构成要件是类型化行为所调整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边界,属于其调整范围而又不符合其调整要件的行为,应当属于自由竞争的合法行为,不宜再依据类型化以外的一般条款加以认定。如《若干问题解释》第1条中明确的“属于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的行为不再适用第2条加以认定的规定,体现了类型化行为在所涉调整领域的穷尽性和排他性。
(二)混淆行为的“三性”及其功能定位
在前文所述搜索关键词隐性使用他人商业标识及服装款式保护等案例中,在不构成市场混淆行为不能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认定不正当竞争的情况下,能否再依据第2条认定不正当竞争的问题,涉及第7条在整部法律中的立法定位以及第7条与第2条的法律适用关系。第7条立法定位的核心是该条是否穷尽了商业标识保护和市场混淆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调整范围。如果旨在穷尽商业标识市场混淆类行为并为其设定边界,不落入第7条的商业标识(注册商标除外)使用就属于自由竞争的范畴。
就立法政策和价值取向而言,基于上述类型化行为列举性规定的“三性”原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应当是为整个商业标识保护类不正当竞争行为划定了市场混淆的法律界限,即只有达到市场混淆标准的商业标识使用,才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而认定为不正当竞争,否则就属于竞争自由的范围。这是一种更倾向于尊重竞争自由的立法理念和政策选择,与上述较为主流的市场竞争价值观更为契合。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与第2条的适用关系,实际上关乎公平竞争观与自由竞争观的权衡。第7条旨在穷尽市场混淆类行为并为其设定边界,不落入第7条的商业标识(注册商标除外)使用属于自由竞争的范畴。如果涉案商业标识使用行为不符合第7条的适用条件但仍可依据第2条一般条款认定不正当竞争,则相当于第7条丧失了为特定类型不正当竞争行为设定边界的价值,也将使第7条沦为虚设。
例如,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在市场混淆以外认定隐性使用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判决,通常以广告主损害他人市场机会和不正当获取交易机会,以及不正当利用他人商业标识声誉等为由。其本质是如何对待“搭便车”“占便宜”“不劳而获”之类的商业成果行为。基于维护竞争自由的政策考量,《反不正当竞争法》并不绝对禁止涉及商业标识使用的“搭便车”,只是禁止达到市场混淆程度的“搭便车”等商业成果侵占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穷尽了商业标识等混淆行为,设定了市场混淆的门槛,达不到混淆程度的“搭便车”等商业标识使用,属于竞争自由的范畴。关键词隐性使用只是触发搜索链接功能,不具有商业标识使用的法律意义,使用其他经营者的商业标识属于“利己不损人”,对于没有损害的行为无须予以禁止。而且,不认定此类“搭便车”构成不正当竞争是一种比较主流的国际态度,契合自由竞争的竞争观。即便如欧盟法院和德国法院,也都倾向于认为此类“搭便车”不构成不正当竞争,只有法国等少数国家在极少数情况以“搭便车”为由认定其构成不正当竞争。如欧盟法院和德国法院认为,广告商选择一个与他人商标相同的标志作为关键词,是为了互联网用户在输入该词进行搜索时,不仅点击来自该商标所有人的链接,还点击广告商的广告链接。此外,具有知名度的商标极易被网络用户作为搜索词输入,以查找与该商标的商品或服务相关的信息或报价。即使将知名商标设置关键词广告,鉴于这是对知名商标所有人的商品或服务的推荐替代选择,也通常都属于相关商品或服务领域健康而公平的竞争。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广告商提供知名商标所有人商品的仿制品、广告商提供的商品负面展示了带有知名商标的商品、广告商对知名商标造成淡化或贬损,利用他人商标的知名度,才构成“搭便车”。
结语
制止混淆行为具有反欺诈的商业伦理意蕴,同时又具有增强市场透明度的经济内涵,能够并需要实现维护商业伦理与促进以自由和效率为标志的市场竞争功能的高度内在统一。制止混淆行为的底层逻辑和目标取向是维护更大的竞争自由和模仿自由,即对于他人商业标识或者相关的商业成果有利用和模仿的自由,但以是否构成混淆为底线。因为,“占有和利用他人的成就是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基石。模仿自由的格言(the axiom of freedom to copy)是自由竞争制度原则的写照。但是,为保护市场中的合法利益,立法机构建立了包括商标权、专利权、外观设计权和著作权等在内的保护性法律框架,以规制市场运作。这一框架原则上构成了获得垄断权的唯一途径,使所有人得以摆脱竞争。”“但是,不正当竞争法基于其他因素而在该框架之外提供保护。这些因素的主要目标是管制市场行为而不是保护市场利益。由此使得未被成文法保护的成果,亦可基于其他因素而获得法律保护。” “无关知识产权的行为产生的混淆可能性仅在仿冒之诉的范围内得到制止”;“除了会导致混淆可能性,模仿和寄生行为并不被认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知识产权专有权以外的商业标识和相关商业成果,应当以属于竞争自由和模仿自由的范围为原则,以构成混淆时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为例外,这是规制混淆行为的理据所在。如前引“歌莉娅服装款式案”二审判决将能够识别商品来源的服装款式纳入当时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商业标识保护范围,不能识别商品来源的服装款式作为商业成果纳入第2条的一般性保护,这实质上是在知识产权专有权和混淆行为之外保护相关商业成果,至少不符合竞争自由和模仿自由的价值取向。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规定的“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既是混淆行为的底线要件,又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化条款与第2条一般条款的适用边界,最终是划分自由竞争与公平竞争的核心界限。混淆行为是在混淆标准之下确定竞争行为的正当性,需要防止以笼统的“搭便车”“不劳而获”之类的公平竞争观念判断商业标识及相关商业成果模仿利用的正当性,防止不适当地扩张商业标识保护边界或者不适当地限制自由模仿的范围。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知产财经立场,平台并不承诺对内容负责,如有相关疑问,请联系文章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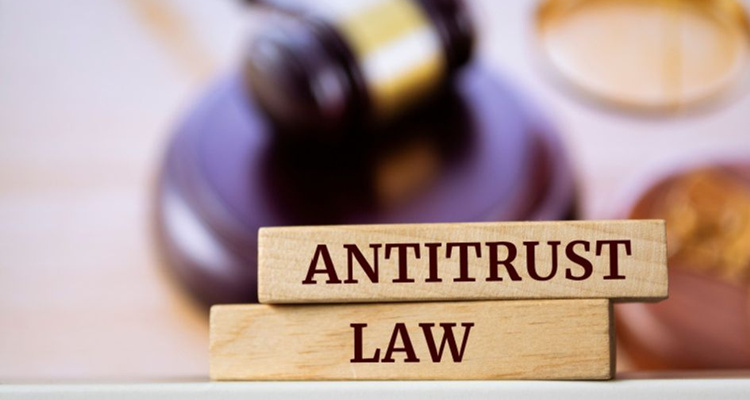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