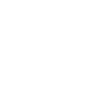涉“靶式流量计”实用新型专利恶意诉讼案
——(2022)最高法知民终1861号
基本案情
2006年3月,某仪器仪表公司的“内置式数显靶式流量计”实用新型专利权因未缴年费而终止。因不服国家知识产权局终止涉案专利权,某仪器仪表公司曾于2017年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又于2018年申请撤诉并获准许。
2006年5月,该公司以其在2005年发现某科技公司、某机械公司生产、销售的产品侵犯了该专利权为由提起诉讼。法院最终认为某科技公司的行为构成专利侵权,判决其向某仪器仪表公司赔偿12.5万元。
之后,某仪器仪表公司以某科技公司在2006年5月至2010年期间仍大量生产、销售侵害该专利权的产品等为由,又分别于2015年、2019年、2020年向法院起诉,索赔350万元、450万元、450万元。其中,第二、三次均在起诉后又申请撤诉,第四次则因未缴纳上诉案件受理费被按撤回上诉处理。在第四次诉讼中,某仪器仪表公司申请财产保全,冻结某科技公司450万元财产。
某科技公司向法院诉称:某仪器仪表公司在明知其专利权被终止的情况下,恶意提起第三次、第四次知识产权诉讼。故请求判令某仪器仪表公司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
裁判结果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某仪器仪表公司赔偿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含合理费用)6万元。某仪器仪表公司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某仪器仪表公司明知其起诉缺乏权利基础,但仍提起第三次及第四次诉讼,导致对方当事人损害,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故意,应认定构成恶意诉讼,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该案的典型价值体现为两个“首”:其系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首例”认定构成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案件;其较为突出地涉及认定恶意诉讼时需考虑的“首要”问题,即权利基础问题。
当事人维权以权利为基础,以事实为依据。权利基础和事实依据是两个概念,首先要有权,然后才谈得上对方有无侵权事实。
关于权利基础,专利权人在起诉前应问自己三个层次的问题,即“过三关”:
一是权利基础“有没有”。在该案中,某仪器仪表公司曾就涉案专利权届满前终止的行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后申请撤诉并获准许。二审判决认为,随着其主动放弃启动权利恢复程序,涉案专利权终止的状态已经确定,且其应当知晓法律后果。
二是权利基础“稳不稳”。有时候,自己的专利权并不稳定,根本经不起无效程序的“考验”,起诉人对此“心知肚明”却“假装糊涂”,法官可能就会对其多打一个问号:“他真的是来维权的吗?”在最高法院知产法庭审理的另一案件中,专利权人隐匿对其不利的专利权评价报告,法院结合其他情况认定其系恶意诉讼。
三是权利基础“厚不厚”。如果专利权价值的“地基之薄”远不足以支撑索赔数额的“楼层之高”,法官可能就会对起诉人产生疑问:“他到底是想干什么?”在该案中,某仪器仪表公司第一次诉讼获得法院支持的12.5万元赔偿,第三、四次诉讼却均提出高达450万元的损害赔偿请求,且在第四次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冻结某科技公司450万元财产。二审判决认为,其明知缺乏权利基础,企图通过诉讼牟取不当利益的可能性极大。
“维权首先要有权,维多大的权首先要有多大的权。”在恶意诉讼案件中,起诉人发起诉讼之易与被起诉人应对诉讼之难“本就不均”,如果起诉人连权利基础的“有”“稳”“厚”都做不到,就能把被起诉人的“事搅乱”、把经营秩序的“水搅浑”,于被起诉人而言“明显不公”,于经营秩序而言“绝不应容”。因此,在恶意诉讼案件中,对起诉人的权利基础进行审查,既是审理思路的“逻辑第一步”,也是实现公平的“正义第一步”。
扫码获取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