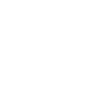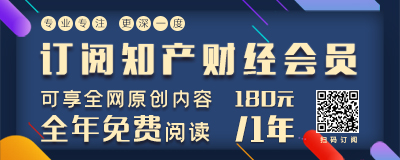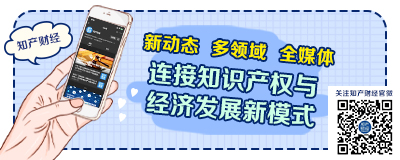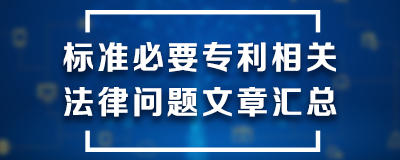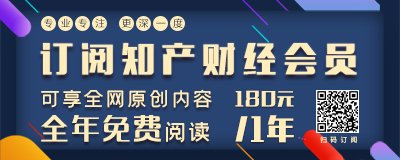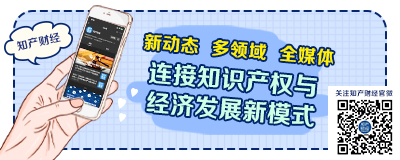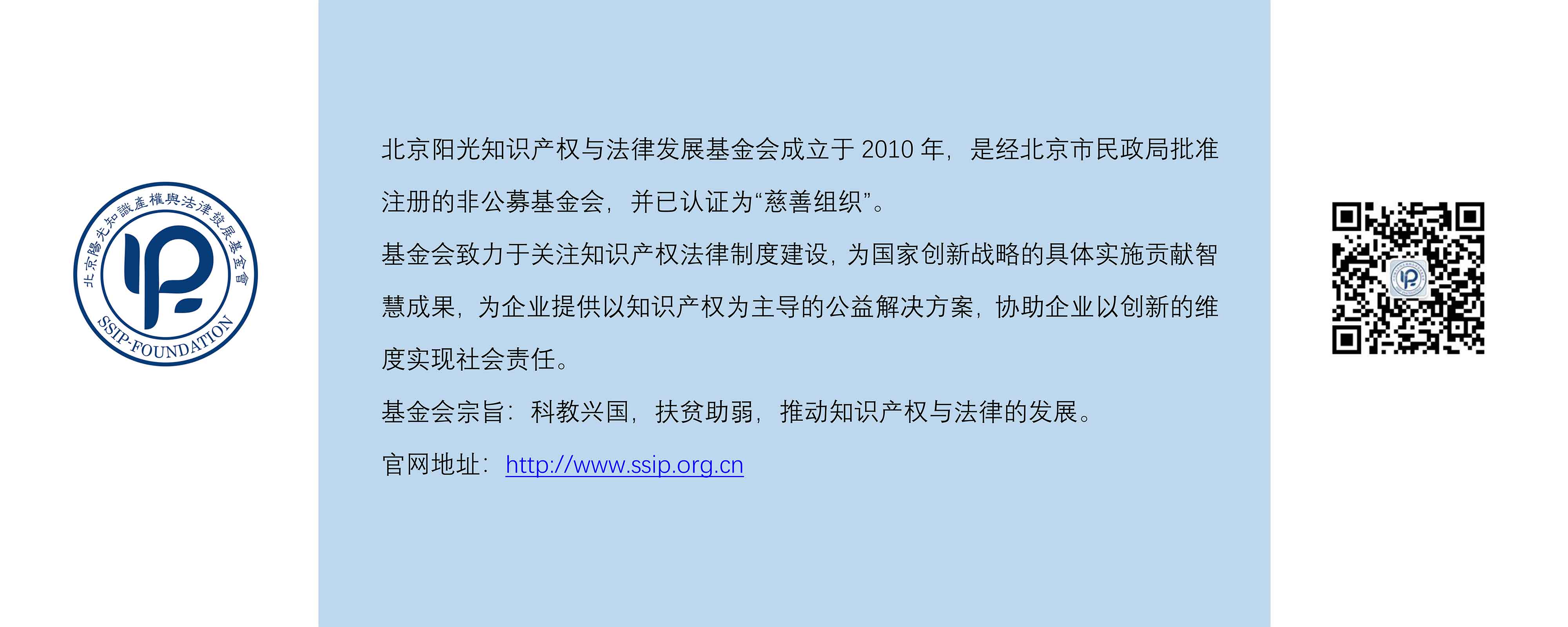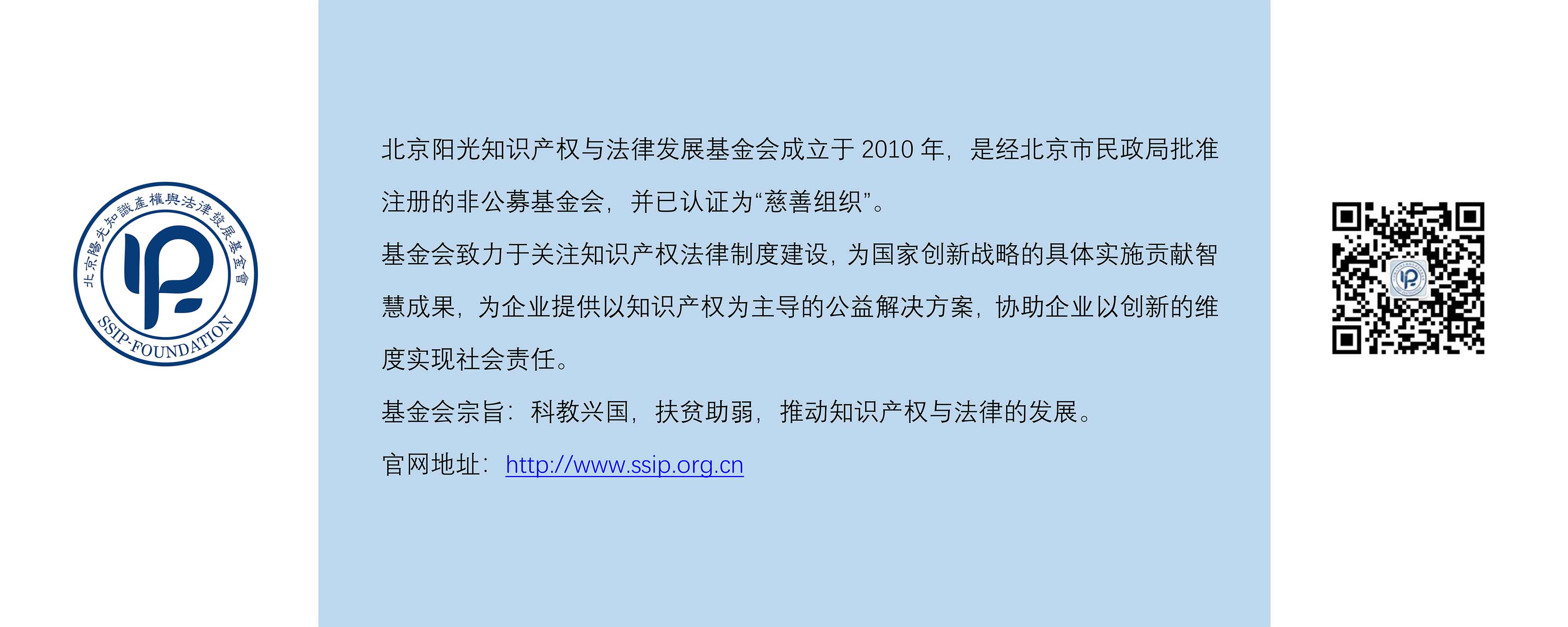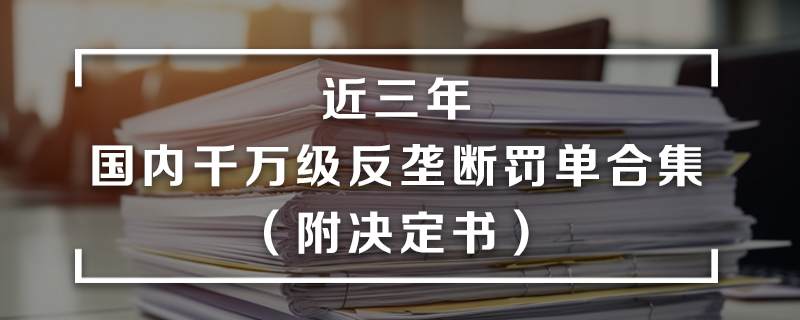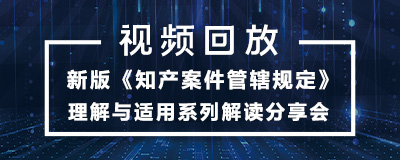私掠(privateer)是一个来自近代欧洲的历史概念,其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支持的海盗行为。16-19世纪,大量取得了欧洲国家颁发的私掠许可证的武装民船曾游弋在海上,频繁攻击他国(特别是敌对国家)的商船、港口乃至军舰,并与授权国分享其获取的收益。在知识产权领域,“私掠”被借用来指称某些实业公司的专利诉讼外包行为,即从事专利技术研发的实业公司(Operating Companies,OpCos)将其专利授权给形式为专利主张实体(Patent Assertions Entities,PAE)的专利私掠者,专利私掠者以此针对其他实业公司发起专利诉讼,并与赞助自身的实业公司分享赔偿金等诉讼收益。实业公司与专利私掠者之间的私相授受,便类似于近代欧洲国家与私掠船之间的分赃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此类现象高发于高科技产业特别是ICT领域的SEP纠纷之中;更令人担忧的是,实业公司与“专利打手”之间的往来交易正从传统的欧美市场逐渐向亚洲市场转移。一场业界不愿看到的“西风东渐”,正悄然上演。
野火燎原:“专利打手”搅局SEP许可市场
Stout在《报告》中指出,目前全球共有近5万个已知有效的5G多制式(multimode)SEP专利族,每个族至少有一个专利已被直接宣布为5G和/或旧一代的必要标准,其中约有超过1100个专利族目前掌握在私掠者手中。对于不事生产与研发的私掠者而言,这些专利毫无疑问地来源于实业公司。私掠者在购买蜂窝SEP一事上表现出了相当高的积极性,据统计,仅在过去十年中,就有超过100起实业公司将SEP转让给私掠者的交易。在以掌握的蜂窝SEP专利族数量计算的私掠者榜单(如表1)中,Sun Patent Trust居于首位,Conversant(康文森)、Sisvel、Acacia等SEP诉讼常客也榜上有名。
表1:蜂窝SEP私掠者TOP 20
在所有已公布的3G-5G通信专利族,排名前20位的蜂窝SEP私掠者约占整个市场的1.1%(基于族数量)或2.5%(基于有效资产数量)。乍看起来,这不过是一个较小的市场份额——然而,标准实施者却依然可能为此承受过于沉重的许可费负担。《报告》根据各种SEP所有人公布的公开许可费率(如要价费率,即“ask rates”),对私掠者与非私掠者所拥有的各种3G-5G SEP专利族的许可费率进行了个体与整体估算。估算结果显示,每个私掠者所拥有的SEP的每个专利族许可费率中位数总和(3G-5G)为每台手持设备平均销售价格的0.00491%,是非私掠者(0.00033%)的14.8倍。
将上述每个专利族专利许可费率的中位数乘以每个相关标准代的活跃单模专利族的总数,便可得出每台手持设备所隐含的(implied)蜂窝SEP许可费累计负担总额。计算结果显示,非私掠者拥有的蜂窝SEP的隐含的ARB为每台手持设备平均销售价格的11.08%;而对于私掠者来说,这一比例达到了惊人的164.07%,远远超出了201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中区联邦地区法院在标志性的TCL诉爱立信一案中所确定的4G标准的ARB范围(即手机平均售价的6%-10%)。不难想见,如果继续听任私掠者扩大其持有的SEP规模,标准实施者的专利许可费负担必将逐步发展至难以承受的程度;而智能手机生产商,也将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利剑高悬:专利私掠危害各方共同福祉
在SEP许可的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原则得到广泛承认的今天,专利私掠者成为了某些台面上的实业公司伸向灰色地带的触手。实业公司与专利私掠者共享着各方面的丰厚收益;与此相对的是,标准实施者、监管机构乃至整个行业生态则共同承受着私掠行为带来的种种负面冲击。
金钱收益是专利私掠者与实业公司最直接也最容易被识别的动机,在这一动机的促使下,某些实业公司与专利私掠者之间的专利转让也呈现出了区别于普通专利交易的新特点。相当一部分实业公司倾向于以较低甚至极低的价格向私掠者转让其专利,进而通过约定累进式的相关专利的后续诉讼赔偿金分成,以期获取丰厚回报。以国际知名移动通信技术公司与Unwired Planet(无线星球)的一桩专利交易为例,双方约定,转让后专利所产生的累计总收益的20%归该移动通信技术公司所有;若累计总收益突破1亿美元,高出部分的50%归该移动通信技术公司所有;若累计总收益突破5亿美元,高出部分中该移动通信技术公司分得的比例将进一步提高至70%。在此类协议的利益驱动下,实业公司与专利私掠者必然以大幅提高许可费率、极限压缩谈判时间并广泛发起侵权诉讼为获利手段,私掠者行权也将无所不用其极,在标准实施者特别是初创企业头上增添不合理的许可费负担,以及诉讼赔偿乃至禁令等迫近威胁。Stout在《报告》中计算得出的私掠者拥有的蜂窝SEP的隐含ARB,便具象化地揭示了这一公开的秘密。
除直接经济利益外,与专利私掠者密切往来的实业公司还可通过专利私掠阻碍竞争对手的产品布局与发展战略,提高其整体运营成本,乃至通过诉讼间接获取目标对手的商业秘密,从而为自身攫取难言正当的竞争优势。更“妙”的是,赞助专利私掠者的实业公司无需直接参与到相关专利的许可与诉讼过程中,从而绕开FRAND原则的约束及标准组织、司法机关的监管,回避与竞争对手的直接冲突,节约自身的行权与诉讼成本。然而,站在反面角度,成规模的私掠行为无疑将造成架空行业规则与法律规范、提高SEP许可费用的不确定性、降低许可过程透明性等一系列巨大风险,不仅浪费司法资源、损害标准实施者的个体利益,同时也将从根本上破坏健康的行业生态,进而阻碍技术的迭代创新,影响全社会的共同福祉。
西风东渐:专利私掠治理亟待新型解决方案
Stout《报告》揭示的另一趋势同样引人担忧:在向私掠者出售蜂窝SEP最多的20个专利权人中,亚洲公司独占11家,包括松下(Panasonic)、夏普(Sharp)、LG、Pantech、Asustek、索尼、三星、华为、中兴等(排名详见图1图2);在所有的SEP私掠交易中,近50%的卖方均为亚洲公司。其中,松下以转让270个通信SEP族的交易量排在首位,其至少已经向IP Bridge、PanOptis、Sun Patent Trust、Intellectual Ventures、Inventergy Global、Wi-Fi One等PAE转让过SEP。在中国国内,上海朗帛等企业也曾将专利转让给Harfang IP (HWT)等PAE。上述PAE大部分都是经常见诸报端的诉讼常客,本质上也均属于专利私掠者。
表2:蜂窝SEP卖家TOP 20
过去十年中,亚洲公司与私掠者的交易保持着整体增势,而欧洲和北美公司与私掠者的交易则趋于减少。显而易见,专利私掠“西风东渐”的浪潮已经到来,亚洲正成为专利私掠者的主要策源地,这值得引起国内移动通信领域企业及监管机构的高度警惕及未雨绸缪。
图1:北美、欧洲、亚洲的实业公司与专利私掠者每年交易数量
相较于更为人所熟知的NPE(Non-practicing Entity,非专利实施主体)概念,PAE几乎呈现出纯粹的投机者、破坏者形象,其危害性更甚。事实上,NPE本为中性词,包括了高校、研究院以及专门进行合理的专利运营的公司等主体;而PAE作为NPE中最为等而下之的一类,则以通过诉讼赔偿、禁令威胁、和解谈判等方式向从事生产的实业公司获取高额专利许可费用为第一要义,几乎不寻求任何许可谈判,其专利质量则往往更为低下,对于推动技术创新的意义也极为稀薄。可以说,PAE或“专利私掠者”更加接近于另一知名度较高的概念,即所谓“专利流氓”(Patent Troll)。
面对PAE及专利私掠行为所带来的超额诉讼威胁,一些标准实施者选择了正面反击。2016年,苹果公司在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Acacia、Conversant等私掠者,指控其不公平地索要过高的专利许可费用,并将矛头直指向二者出售了数以千计专利的国际知名通信技术开发公司。苹果在诉状中指控Acacia、Conversant与该通信技术公司“共谋”(collude),试图向苹果及其他智能手机生产商索要和诈取(extract and extort)过高的许可费用。苹果表示,上述两方的此类私掠行为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反竞争阴谋”(a continuing anticompetitive scheme),这一表述言简意赅地道出了私掠行为的本质属性及其利益关联。
在另一起专利侵权纠纷中,一家名为VLSI的PAE从某半导体企业获得专利后,在美国特拉华州地区法院起诉Intel专利侵权,并向法院主张高达41.3亿美元的赔偿金额。据路透社报道,在Intel不断请求和法官不断要求VLSI公开专利诉讼相关的诉讼基金和经济利益等信息后,VLSI选择撤回对Intel的起诉且不得再诉(dismiss with prejudice),并承诺不会使用涉案的5件专利对Intel的供应商或客户提告。路透社在报道中还提到,VLSI和Intel双方都无需为结束此次诉讼而向对方支付任何费用。这样一场看似无疾而终的诉讼,再次揭示了专利私掠者的“打手”本质,也暴露出其背后复杂的利益关系。结合专利私掠者近年活跃的交易行为来看,可以预见,类似此案未来或许还将继续上演。
除司法途径外,部分大型实业公司也试图借助行业共治打击私掠行为。2014年,谷歌、佳能等企业主导成立了非营利性组织LOT Network,致力于通过实业公司之间的密切协作,打造PAE免疫机制。加入LOT Network的实业公司若将其专利出售给PAE,或其专利被出售给其他实业公司后再次出售至PAE,则该专利对LOT Network成员的许可将自动生效,无论PAE还是其它公司都不能以其对LOT Network成员提告。如今,LOT Network已拥有超过368万件专利资产和超过2800家成员,其中就包括中国的腾讯、小米、阿里巴巴等公司。LOT Network的出现无疑为业界应对专利私掠现象提供了一套颇具价值的参考方案,有助于解决部分问题;不过,在ICT领域,目前仍有诸多大型实业公司尚未加入这一组织,部分实业公司或想通过专利私掠的方式继续获得超额收益。而在其他技术领域中,连类似的尝试都还付之阙如。
总结而言,专利私掠是一个亟需专利权人、标准实施者、监管机构等各方共同重视与参与治理的棘手问题;数据所反映出的专利私掠行为“西风东渐”的大趋势,更进一步放大了这一问题的急迫性。面对专利私掠所带来的危险的利益失衡,为避免亚洲市场成为专利私掠行为新高地,维护全球ICT领域的良好竞争秩序,对私掠者乃至其背后的实业公司的评价也应突破关注主体地位适格与否的法律内框架,将思考的起点拨回专利制度的初衷,方能得到符合历史尺度的认识以及更具实用性、普适性的解决方案。此外,拥有专利的实业公司不仅要算个体账,更要以长远目光算大帐、算行业账,确保行业的健康发展,让科技成果和产品真正惠及千千万万的消费者。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知产财经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