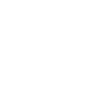作者:王倩 天津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 法官
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相约在云端,就前沿的问题展开讨论。刚才大家在前面的发言我深受受启发,在接下来的这十几分钟的时间里,我主要是从审判实践出发,梳理在司法案件当中应用市场责任承担的具体考量因素,分析裁量者思考的轨迹,也希望能通过对生效司法裁判的分析,挖掘出背后隐藏的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
一、应用商店侵权责任认定的实证分析
首先,我对于涉应用商店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进行了实证分析。由于我国裁判文书从2014年正式全面公开,同时又受限于文书上网率等因素,所检索到的裁判文书并不一定代表相关案件实际审结的数量,但是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近年来涉及应用商店侵权责任的案件裁判情况。在裁判文书网选择“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由,同时以“应用商店”“应用市场”为关键词,共检索出了涉及到应用商店运营者作为被告的裁判文书共156篇。
从审判的年份上来看,案件的数量从2013年开始有所增长,在2017年有所回落,2019年又开始急剧上升。从地域来看,北京案件数居首、天津第二,其他案件分布分布在上海、江苏、山东等地法院。
图1:“应用商店”侵权案件审判年份分布情况
在梳理案件的过程中,我注意到涉及苹果公司的案件数量比较突出,所以我下面也就涉及苹果公司“App Store”的案件进行梳理。 截止检索日,涉及到苹果公司的相关案件有126件,从审判的年份案件数量变化来看,和整体案件的数量变化趋势是差不多的,2016年有所上升,2017年又有所下降,之后又有所回升。在审判地域上,苹果公司的案件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和山东的各地法院也都有所涉及。案件数量变化反映了该类案件数量回升的态势,应用商店的侵权行为方式更加多样,权利人的维权需求不断增强,对行业发展和司法审判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图2:涉苹果公司“App Store”侵权案件审判年份分布情况
二、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应用商店被诉侵权行为样态
以往我们在讨论应用商店被诉侵权行为的时,主要是围绕间接侵权的情形,既有智能手机应用平台上提供App的下载,如阿里公司在其经营的智能手机应用市场“云手机助手”提供“56视频”应用程序的免费下载,又有智能电视应用平台上提供的涉案App的下载,如心梦想公司在其经营的电视应用市场“沙发管家”中提供了“电视猫视频”应用程序的免费下载,此类案件一般会以应用商店的经营者以及涉案App经营者作为共同被告,当然也有部分案件权利人基于当事人赔偿能力的考虑,仅起诉应用商店的经营者作为唯一被告。以上行为主要是涉及到帮助侵权的认定问题,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直接侵权的情况其实也是不容忽略的,比如说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诉苹果公司案实际上和李承鹏诉苹果公司案在事实部分是类似的,但是在判决结果却相差甚远。“李承鹏”案,法院认定苹果公司构成帮助侵权,但在“大百科”案中,法院认定苹果公司构成直接侵权。导致这样判决结果的原因是“大百科”案中苹果公司在庭审的过程中未能提交涉嫌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用户的相关资料,法院最终认定苹果公司没能证明被诉侵权行为是第三方实施,从而认定涉案应用程序是苹果公司自己发布的,苹果公司承担直接侵权责任。除此之外,在中文在线诉腾讯公司“刷机精灵”案中,由于涉案应用市场直接提供了涉案应用程序的下载服务,而且在下载的过程中,既没有出现任何第三方网站,也没有显示是来自其他第三方的跳转过程,虽然被告辩称涉案应用程序链接了第三方的网站,但未无法证明其主张,法院最终直接认定被告构成直接侵权。 我在这里强调直接侵权类的案件,也是为了给应用商店经营者敲响警钟,因为这类案件认定不仅体现出行业内普遍存在无法找到涉案 App开发者的乱象,还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应用商店审核开发者身份真实性的必要性。
三、应用商店侵权责任的考量因素
认定应用商店经营者是否承担侵权责任,需要考察其对具体被诉的侵权行为是否存在过错。通过梳理生效裁判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应用商店经营者的主观过错即主观上的明知或应知。
第一,获利与否及获利方式。在司法实践中,获利与否本身就是判断应用商店是否具有过错的重要考量因素,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把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纳入到了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中。在判断获利情况时,法院主要是通过应用商店和第三方软件开发商之间的用户注册协议和软件上传协议的内容以及上述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进行考察。如协议中约定合作共销、利益分成等内容,则容易被认定其直接参与了销售,属于直接获利。李承鹏诉苹果公司案,在苹果公司按照3:7的固定分成比例收费的情况下,法院推定苹果公司直接获利。在玄霆公司诉机客公司“机客网”案中,法院也是通过协议查明应用商店与开发者之间的3:7分成合作模式,认定被告因从被诉侵权行为中获利构成侵权。当然司法实践中,也有应用商店没有获利的案例,在中文在线诉阿里云公司“云手机助手”的案件中,由于没有证据证明阿里公司从涉案的软件中直接获得了经济利益,所以法院认定其不构成侵权。在部分案件中,被告会抗辩说其提供的是免费下载,或者抗辩其收取的是服务费和广告费。此种情形,我认为应当整体考虑平台的收益模式,进而判断这部分收益的性质,是否是免费下载使用并不是认为平台运营商有过错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管理控制能力。对应用平台的管控实际上就是对被诉侵权行为的管控。这种管控能力的大小可以通过是不是能够产生实质性影响来衡量。在李承鹏诉苹果公司案中,法院通过苹果公司掌握了第三方开发的方向和标准,向开发者提供了一系列辅助开发工具,同时控制分销这三个因素来认定苹果公司根据自身规划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政策及协议条款,对苹果应用平台具有很强的控制力和管理能力。
第三,选择、编排和推荐的情节。选择、编排和推荐一般是应用商店基于网络用户的用户体验而主动设置的,一方面会为网络用户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指引,可以增强应用商店用户粘性,进而增加更多的经济收益,从另一方面,权利人在被侵权时,会因为上述行为遭受更大的损失。此种情况下,提供链接服务的应用商店主动对被链接的内容进行了人工的选择、编排、整理,较由网络用户直接通过搜索指令获得链接服务,应用商店应负有更好的注意义务。如千杉网络诉心梦想公司“电视猫”案,心梦想公司在首页中列明了热门的应用以及最新上架应用的分类。上述选择、编排和推荐体现了应用商店对于设置栏目的相关程序内容具有接触可能的,进而可以认定其构成侵权。在中文在线诉阿里云公司“云手机助手”案中,有一个情节可能更加明显,通过手机助手进入涉案视频网站与通过网页版输入网址进入网站,两者呈现的栏目数量、展示图片、文字内容,整个布置编排都存在较大差异,更加说明了应用商店根据自身需求进行了相应的编辑和整理,即其应该知晓涉案的 APP上存在着大量侵权影视作品。
第四,涉案App的浏览、下载量、涉案作品的知名度、下载量等其他因素。法院在侵权责任认定的过程中,App下载量、涉案作品知名度等是考量认定赔偿数额的重要指标,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考量是否构成侵权的标准。通常来说,如果涉案作品是影视作品或者是知名歌手的音乐作品,对涉案App传播的内容是否属于正版的播放内容推定应用商店是有所认知的。中青文化公司诉百度公司的“百度手机助手”案中有两个比较突出的情节,一个就是涉案作品在百度手机助手当中,下载量已经达到了10万余次,而且还有一个情节为涉案作品名称和它应用程序的名称是相一致的,此时法院直接认定百度公司没有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百度公司存在过错。
四、应用商店预防化解侵权风险的建议
最后,基于对相关生效判决的梳理,提出几点应用市场的预防化解侵权风险建议。
第一,严格进行应用程序上线前的审核,加强对应用开发者的管理。在开发者提供申请信息时应用商店即进行工商核验,或者通过人脸识别的方式审核相应的信息,同时还可以考虑设置一个侵权黑名单,或者侵权保障金制度。
第二,严格对经筛选、编排、推荐等设置的专栏实时审核。这一点是主要是针对实践中法院在认定侵权行为的过程中,可能考量的因素,应用商店对于筛选、编排、推荐等设置的栏目应当进行实时的审核,对于热门板块可以进行人工审核,持续关注。
第三,积极履行与应用程序开发者协议相关内容。提这一点的原因在于,在具体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中,开发者协议中约定了开发者不得侵权,但是应用商店没有按照协议要求开发者提供相应的版权证明。应用商店运营主体应当谨慎地制定协议内容,避免协议流于形式,让侵权人有可乘之机。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